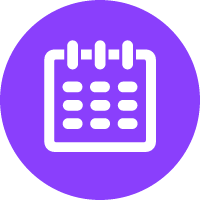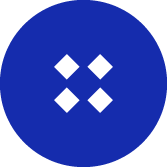所有語言
分享
狂飆200天:進退兩難的中國大模型團戰
來源:暗涌Waves
文 | 何麗芯
編輯 | 於麗麗、劉旌

極速200天
兩個月前,「暗涌Waves」曾向一位投資了王慧文光年之外的基金合伙人提問:中國創投史上,哪個公司在創辦之初就眾望所歸、並且最終也擁有美好結局?
“說實話,我很難想到。”這位投資人答道。
作為一位AI行業的“門外人”,王慧文的殺入格外有戲劇性,最終能有多大的勝算?
沉吟片刻后,這位合伙人打趣說道:“至少,老王是一個有爭議的人。”他的言下之意是,對於多數頭部美元基金來說,大概沒有理由不投資王慧文這樣“能夠集資源、錢、以及號召力為一體的大佬”。
後來的故事眾人皆知。伴隨着王慧文確診抑鬱症,光年之外被美團接手,這個大模型創業潮中引發最多關注的故事戛然而止。
當我們提出那個問題時,中國大模型的創業還在狂飆之時。人們無比相信那個比“移動互聯網大10倍”的平台級大機會:在GPT-4推出不過20餘天時,已有超10餘家創業公司坐上大模型牌桌,總融資額數十億美金。此後包括大廠在內的20多家公司公布了自研AI大模型,“就連上古神仙的名字都不夠用了”。
頃刻間,光年之外的戲劇化故事,似乎應驗了通用大模型很難屬於創業公司的預言。越來越多的公司開始逃離大模型神話。
時間回到一年前。在舊金山第18街和Folsom街交叉口,有一座不起眼的灰色三層小樓,很快它將名聲大振——這是OpenAI的辦公所在地。一位硅穀人士告訴告訴我們,紅杉中國創始及執行合伙人沈南鵬和OpenAI溝通之後,“大為震撼”,這位如飢似渴的投資人而後便令團隊“動起來!”
紅杉再次展現出了它一貫的戰鬥力。“在國內投資人中,Neil的認知應該是跑到最前面的。”上述人士表示,沈南鵬開始更大力度地抓AI投資,“能見的人都見了一圈”,其中就包括沈向洋、楊植麟和阿里CTO周靖人等。而外界所能看到的是,2022年9月,紅杉官網發表了《Generative AI, a Creative New World》一文,第一次提出生成式AI的概念。
“從硅谷到國內,創投風潮的傳遞大約會有3個月的延後。”一位美元投資人對「暗涌Waves」表示,所以ChatGPT在去年11月底發布,直至今年春節后,國內關於大模型的討論才瞬間熱烈起來。
春節后,踏上去硅谷航班的源碼資本合伙人黃雲剛,本來還想一併考察SaaS、Bio-tech,但最後幾乎所有會議都和AI相關。此時想約OpenAI的人已不再容易:其員工後來基本關閉或隱藏了包括LinkedIn在內的各類個人聯繫方式。
這可能是過去十年、從硅谷到國內最快的一次共識收斂。
在生成式AI面前,本就力竭的移動互聯網,頃刻仿若陳舊之物。新一輪的世界交接儼然已經開始。
人人都能感受到市場的躁動。2月中旬,在微軟戰略孵化器組織的一次AI分享會上,人頭攢動,茶歇區被擠滿,連咖啡師都在櫃檯里拿着手機拍PPT。牆上各種NFT印刷品的包圍,似乎又在提醒人們這裏數月前還屬於Web3。
彷彿一種應激反應,國內投資人一頭扎進AI,卻又發現大量功課要做。多位投資人在採訪中不約而同稱自己“還在學習”,以及反問:你們最近還跟誰聊了?
今年3月,在接受我們訪談前一天的凌晨,阿爾法公社創始合伙人&CEO許四清正在“讀paper”,然後接到一位成功創業者師弟的微信,問能否一聊AI。後者驅車20公里來到他的住處,兩人一直討論到凌晨三點才散去。
創投界的大小人物紛至沓來,王慧文也是群情激昂中的一份子。曾有接近他的人對「暗涌Waves」透露,王慧文對大模型創業的態度變化非常之快,原本他只是計劃以投資的方式入股一家公司,但在三天內就決定躬身入局。
但風口總是不長命。儘管嚴格來說,相比於移動時代尾聲的眾多議題,大模型或AGI無疑是一個真命題。在GPT-4推出不過20餘天時,市場已明顯感受到,在這個註定是少數人的遊戲中,國內通用大模型的創業潮首戰已基本終結。
6月底,獵豹移動CEO傅盛和金沙江創業投資基金主管合伙人朱嘯虎在朋友圈的互懟,在體現投資人和創業者視角種種差異的同時,也显示出一種異常冷靜的共識:有機會,但不會是BAT式的大機會。
短短200天,更多的投資人和創業公司的焦點開始往垂直大模型或中間層、應用層遷移,而那個狂熱的平台級或顛覆性的大機會,也逐漸被更現實的“零零散散的小機會”替代。
真格基金管理合伙人戴雨森曾對我們說,隨着一波波新技術的興衰,AI在創投界不斷進入冬天和春天。每一次看似高蹈的技術理想面前,都懸着一把難以商業化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這次也沒有例外。

浮沙上的高塔
共識可以快速形成。
ChatGPT的發布讓國內市場的FOMO情緒在年初達到頂峰,團隊和資金快速集結大模型。牌桌上的选手,分為:互聯網創業派、大廠派,以及來自高校和研究機構的學院派。
共識也可以快速瓦解。
註定是燒錢遊戲的屬性,算力、數據和人才的門檻,以及當下資本市場的變化,讓“大模型是否是創業公司的機會?”的詰問一直懸在頭頂。
事實是在今年4月,「暗涌Waves」就注意到國內通用大模型創業潮的首戰,已基本終結。這一說法後來也得到一些投資人證實,“就這些了”,此後聲稱要入局大模型的創業公司基本絕跡。
在一位一級市場觀察人士看來,關於大模型,不光創業團隊,敢下場的大基金也只有少數大名字,而且機構主要基於賭人的邏輯,前方還有漫長的證明題要做。
和傅盛論辯完的朱嘯虎,第二天就在朋友圈表示,他的核心觀點是:不要迷信通用大模型,因為明年GPT-3.5就成commodity(通用基礎設施),而3年後,GPT-4也會是。
這背後正是關於大模型的另一重隱憂:底層的大模型本身在變,而未來很可能大量開源,或者1-2個頭部廠商贏者通吃。如此一來,中國大模型創業的價值與投入就根本不成正比。
至於那個眾人言說中的“比互聯網更大的機會”,在戴雨森看來,立足點是“能做出可以使用工具、解決任務、分解任務的AGI”,而能實現這一點的團隊,即便在世界範圍內都很稀缺。
前不久,在Waves大會的一場圓桌論壇上,中國人民大學高瓴人工智能學院盧志武教授,就質疑了所謂“國產大模型的春天”。在他看來,這不過是很多公司在“微調國外底座模型”的假象。
現實也的確如此。一位AI創業者告訴我們,很多聲稱要做大模型的創業公司,其實從一開始就是在用Supervised Fine Tuning等快捷技術,做一個“還可以的”語言大模型出來,真正有資金和技術實力去挑戰GPT4的團隊和項目屈指可數。
更多創業公司開始向醫療、法律等垂直大模型以及中間層、應用層遷移。王慧文的光年之外,以及王小川的新公司,後來都選擇了同時做大模型和基於模型的應用。
“42章經”曲凱發布的數據显示,以他的體感,前一段拿到融資的AI項目中,做底層模型的大概有10%-20%,做infra/中間層的有20%-30%,做應用層的有60%-70%。其中如果把還沒拿到錢的也加進來,做應用的估計至少是95%+。
但垂直大模型以及應用這條路也並非坦途。對創業公司來說,垂直領域的場景和數據很難獲取。而它所構建的能力又不能是通用大模型輕易覆蓋的。
像infra/中間層,一位投資人曾在社交媒體上表示,旨在滿足數據採集、標註、模型調度等MLOps需求的創業公司,會面臨“中間商難賺差價”的夾心尷尬——前有免費開源工具,後有雲廠商打包工具和服務。同時,“國內客戶付費習慣仍然沒有很好地養成,尤其在企業開支緊縮的經濟恢復期”。
在Waves大會上,真格基金戴雨森提到,在中國做2B服務,會受到市場付費意願、客戶採購方式特點的限制。“中國互聯網之前一大特點,就是要直接找用戶收錢很難,很多時候都是羊毛出在豬身上。”像OpenAI和Claude在美國可以直接通過公有雲賣API服務,而在中國只提供API還不夠,“很多做大模型的公司針對企業客戶,現在是連服務器帶模型一起賣,還得提供訓練和微調服務”。
上述在社交媒體發文的投資人還提到,應用層項目可以分為兩種:那些垂直場景里深耕的老項目在积極接入大模型,手握數據做微調;而新項目談格局為時尚早,在大模型的迭代能力被充分釋放前,很容易“速生速死”。
這在海外市場已有表徵。例如去年尚風頭無兩的美國獨角獸Grammarly和Jasper,在GPT4發布后,現有功能即被代替,價值迅速被攤薄,朱嘯虎公開稱“這兩家公司或將很快歸零,根本守不住”。
今年3月,OpenAI發布論文開源了新模型代碼:效果一步成圖,1秒18張。有人因此評價“擴散模型Diffusion的時代結束了”。而此時距離後者成為2022“AIGC元年”誕生的重要技術基石,以及基於此帶來許多模型的湧現,還不到一年。
所以這一波AI創業者、尤其是應用層公司,始終存在於一個左右互搏的困局裡:不做,錯過了是輸;做了可能很快被替代,同樣是輸。
在Waves大會上,崑崙萬維CEO方漢提到,他和中國最頂尖的產品經理交流后發現,對方還處在很懵的狀態:“這一波大模型遠超產品進展”。隨後的獨立演講中,獵豹CEO傅盛快速反駁了這一判斷:“產品經理並不懵,很多已經在行動”。但顯然至今,還沒有令人滿意的殺手級產品出現。阿里巴巴、百度推出大模型的當日,股價均不同程度下跌。
這些特性也造成了一級市場的一種奇觀:除了紅杉中國、真格、源碼、五源、IDG資本等機構,“機構新出手很謹慎,更多积極在促成老項目和portfolio往AI方向轉,從而多出去融錢”。
在一些投AI投資人眼中,不光是模型升級問題,如果AI安全衝突——這個普羅大眾更關心的問題——進一步加劇,也可能會讓AI浪潮再次進入低谷,這一次的AI信仰還能持續多久?

十年AI夢
十餘年來,AI風口在創投界一直迴環往複地出現。
技術路線的不停演化,讓這個行業充滿了那種“槍出現之前,研究如何能磨一把更快的刀”以及“發現未被識別的槍”的故事。
如同深度學習路線在2012年以前被忽視一樣,在AlphaGo最熱的2016年,通用人工智能被業界普遍認為不可能實現。“2018年GPT1推出,在當年看來是離經叛道的路。”綠洲資本創始合伙人張津劍曾對我們描述,當時的行業主流路線是垂直模型、人工標註,“彷彿雕花”,而GPT做通用,“強行用大量數據硬懟,在學界看起來很粗魯”。
出門問問創始人兼CEO李志飛回憶起2年前開始做大模型的經歷:團隊頂着很大壓力,技術總監幾度提出離職。而此時其實距離谷歌2017年發表Transformer模型、為通用人工智能打開了第一扇門,已經過去了三年,然而少有人識別出背後的意義。
追溯歷史,從1960年代人工智能概念在學界被提出以來,僅本世紀就誕生過兩次AI浪潮。
2012年,在全球最大規模的視覺識別比賽中,時年65歲的Geoffrey Hinton教授帶領兩名學生拿下冠軍。成功來源於在一種新的AI研究範式中找到突破:以深度學習為代表的神經網絡派,從此前沉寂20餘年的學術邊緣研究,一躍成為正統主流。
之後十年間,深度學習成為大多數人工智能企業的底層技術基礎,並從學術走向產業,在視覺、語音和語義技術等領域率先應用。
在中國,語音識別領域,誕生了出門問問、科大訊飛、雲知聲等公司,圖像識別領域,則出現了AI四小龍曠視、依圖、商湯、雲從以及第四範式等。
而在2016年,谷歌AlphaGo在人機圍棋比賽中以絕對優勢擊敗世界圍棋冠軍李世石,讓“機器智慧戰勝了人類”的現實,第一次在大眾層面上被廣泛認知。這迅速引發了全球AI軍備競賽,並很快迎來國家政策層面的支持。
在這場AI熱潮中,大廠宣布All In,陸奇空降百度,騰訊、字節等相繼組建AI Lab,阿里達摩院成立,馬雲喊出“三年投入1000億元”的豪言。
各大科技論壇上,人們樂此不疲地探討“奇點已來”和機器人三定律,投資人篤信,人工智能將是繼蒸汽機、內燃機和互聯網之後的第四次生產力革命。
彼時的創投行業正面臨投資主題的缺乏(與當下不無相似),幾次互聯網大併購相繼落幕,平台型機遇消退,巨頭的觸角無處不在。AI和直播短視頻、共享單車等一起,接棒成為熱門賽道。
AI投融資趨於狂熱。有報告显示,2016年全球AI融資規模近百億美元,相當於2000年到2013年13年間總融資額之和。一個側面佐證是,在2016年全球股市低迷的情況下,英偉達股價依然漲了3倍。
但疲態很快顯現。2019年,中國在AI領域的投資額與投資筆數大幅下降,9成AI創業公司處於虧損狀態。猛烈降溫開始了。
據IT桔子等數據显示,2014年至2018年,中國人工智能領域的IPO退出平均回報僅為1.83倍,2018年全年有將近90%的人工智能公司處於虧損狀態。2019年,“投資人逃離人工智能”刷屏,經過幾年凋敝,除聯想之星、創新工場等機構外,國內真正在持續關注AI的投資人寥寥,大基金也幾乎沒有專人在長期覆蓋。
可以說,除了少數早期投資者落袋為安,AI至今是一個沒能讓投資人賺到大錢的賽道。
一則至今被反覆提起的投資人舊聞,或能代表其間慘烈:成立於2013年的格靈深瞳,傳言公司在拿到天使輪后,徐小平在飯局上稱其至少估值5000億美元,而沈南鵬認為1000億美元比較實際,最終妥協在了估值3000億美元的中間數上。而現實讓所有人意外,時隔9年,經歷了流血上市的格林深瞳去年終登科創板,當前市值是65億人民幣(以7月6日收盤價計算)。
AI十年,至今還走在阻且長的道路上。
在曠視的首位投資人、聯想之星總裁/主管合伙人王明耀看來,十年前的AI創業者處在摸索階段,背景大多來自學術界,對變現的思考不甚清晰,加上並不成熟的產業配套,共同導致了AI商業化道路的漫長。
2011年,聯想之星決定扶持三位年輕人走上創業之路,曠視當時估值僅1400萬人民幣。天使輪后,為避免人民幣無錢可融,公司才轉為美元架構。彼時資本市場的低預期,讓“早年的AI創業者起步很難”。之後,曠視從CV遊戲一路到相親社交、商品推薦的嘗試都不順利,直到2015年與支付寶開始人臉支付合作。王明耀回憶,公司甚至“成立5年才拿到第一筆政府安防訂單”。而今天的市場,不可同日而語。
這也讓創投界對AI的又一次狂熱,顯得格外義無反顧。而這次技術進步最大的意義不同在於——AI第一次具備了通用的可能。
如果說過去十年深度學習的兩輪AI創新,仍然是點狀分佈,是面向特定任務的智能、作用於垂直行業,這一輪的大模型則是李開復所說的“從孤島到大陸”的進步:無需人工標註,模型規模大,具備跨領域能力。
技術突破對舊世界的改造是劇烈的。一位互聯網投資人對我們說,新浪潮之下,像商湯、曠視這樣的大公司,至少還留下了大量算力和經驗儲備。而對更多的AI企業來說,隨着技術的演化,或將“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

回不去的舊世界
“Holy shit!”DCM董事合伙人林欣禾脫口而出。
這是22年初聯繫到Tiamat創始人青柑時,林欣禾第一次看到文生圖效果的下意識反應。
這位親歷互聯網浪潮的成功創業者,一直活躍在一線的古典互聯網投資人。在對「暗涌Waves」描述當時情境時,他毫不掩飾驚訝,並堅定認為“新一代AI浪潮真的來了”,“不再以TMT時代的推薦為邏輯,而是直接替人完成所有事,人連鼠標都不用動。”
儘管對AI的投資還在迷霧中行走,甚至在短期內都將保持低沉,但這不妨礙它持續向舊世界開炮:像SaaS、出海等大量原有商業模式,面對即將被AI改寫的命運。
一位長期關注企業服務的投資人認為,未來中國的SaaS公司,甚至所有2B企業,都應該是人工智能公司,軟件將被智能即服務所替代。
AI一方面降低服務成本&提高人效,另一方面打通服務的流程環節。如果仍然是一家傳統的軟件公司,“那基本沒戲了。”
風暴同樣席捲原有的AI創業者,技術路線的失靈,帶來的危機只會更甚:上一波基於深度學習做垂直小模型的AI公司,要麼革命,要麼死亡。
李志飛舉例,以前很多做NLP的人,總覺得這些變化影響不到自己,“過去有PhD或教授專門研究語法解析、詞性標註,未來這些中間環節都會消失”。很多從業者如今終於意識到,未來就不應該存在一個專門做機器翻譯、問題回答或語音識別的工種。如果不轉型,就將面臨失業或工作無人關注的窘境。
在一些投資人看來,當生產力的供應結構被重新塑造,無限量的初級工程師將由AI替代。被長期作為中國商業自信敘事一部分的“工程師紅利”,或將不再存在。
心識宇宙創始人陶芳認為,面對AI,接下來只有兩種人:“溺水者or淘金者”,他進而反問到:“蒸汽火車來的時候,難道隻影響馬車司機嗎?”
真格基金合伙人劉元則表示,對於投資人和創業者來說,這意味着“三五個人可以干翻大廠的機會”又重新存在了。他甚至感覺,“之前所有的積累恰好是為這一刻準備的”。
劉元在2014年入行,作為早期投資人,他“偶爾覺得有些生不逢時”:錯過了移動互聯網最好的2011-2012,後來的雙碳、新能源、汽車等風口又極度資本密集。而突然,TMT投資人所熟悉的數據飛輪、顛覆式創新、產品思維同理心等經典理論,“好像又重新有用了”。
在訪談中,劉元反覆向我們提到維特根斯坦的那句名言:“語言的極限就是世界的極限”。他說,這是AGI更令他激動的部分:如果人的思維就是一個語言過程,那文科生臆想中的世界極可能在語言大模型上實現。
目前,經過第一階段的角逐,許多投資人們似乎更看好大廠的大模型試驗。
不過,正如不久前下場大模型的幻方創始人梁文鋒所言,“市場是變化的。真正的決定力量往往不是一些現成的規則和條件,而是一種適應和調整變化的能力。“而這或許才是創業公司的縫隙。
林欣禾在歡呼新時代到來的同時,也認為當前很多大模型有“因為缺乏應用而受阻”的可能。他類比五六年前美國AR/VR賽道的火熱:谷歌眼鏡燒錢無數,但至今未做出來。何況在這波AI革命中,軟件尚未和硬件充分結合,“很多事情We still have to see”。
但無論如何,在林欣禾看來,ChatGPT就像一道玻璃門,一旦跨過就再也回不去了:“AI is the new internet.”
這場至今不過200天的創業潮,或許正是未來創投故事的典型樣貌:道路無疑正確,但註定漫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