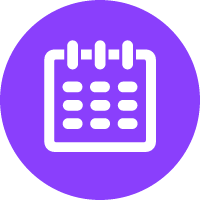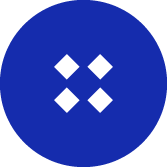所有語言
分享
ChatGPT生成的內容,是否享有版權?
朱開鑫 騰訊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當AI只接收來自人類的提示文本,並輸出複雜的文字、圖像或音樂時,創作性的表達是由AI技術而非人類確定和執行。上述內容不受版權保護,不得註冊為作品。” 這是2023年3月16日生效,美國版權局關於AIGC版權註冊最新指南的內容。1這意味着,目前在美國ChatGPT類產品生成的內容將不會被註冊為作品。
近期,Open AI“GPT4”新系統的發布和百度“文心一言”的推出,也將國內對AIGC版權問題的探討再次推向高潮。本文希望結合國內外在AIGC版權領域的既有案例實踐,就目前ChatGPT類產品生成內容的版權屬性、權利歸屬與責任機制等各界關注的問題,嘗試做一前沿性理論探討。
以案說法:美國版權局率先拒絕對ChatGPT類產品生成內容進行作品登記
2023年2月21日,美國版權局在“黎明的扎利亞版權註冊案”2(以下簡稱“Midjourney案”)中,率先對ChatGPT類產品生成內容的版權屬性做出否定性裁決。“用戶利用Midjourney這一AI繪圖工具生成的漫畫內容不構成版權作品,因為在圖像生成過程中3沒有自然人的創造投入,而是由Midjourney自動隨機形成”。在3月16日的指南中,美國版權局再次明確了上述立場“根據對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理解,用戶對於輸出的內容不具有創作性貢獻和控制,應當拒絕版權註冊申請”。4
“Midjourney案”中,申請人曾反駁道,“和畫筆以及其他繪圖軟件無異,Midjourney在漫畫生成過程中僅僅是被用來完成用戶內心希望呈現圖像的工具。”對此,美國版權局表示,用戶無法預測和控制Midjourney 最終輸出的圖像形態,這一重要事實使得其與傳統繪圖工具存在本質區別。當使用畫筆或一般繪圖軟件時,畫家可以選擇構圖的起點,通過工具和材料的具體選擇實現線條粗細、色彩明暗等的具體修改,並採取自身希望的步驟來形成最終的圖像,整個過程相當於畫家“將自己內心的最初構圖一步步賦予外在的表現形式”。
而Midjourney則是以一種用戶不可預測的方式直接生成圖像,其過程可以概括為:首先,向用戶界面輸入一段描述“目標圖像”的提示文本;其次,選擇Midjourney輸出的一個或多個圖像來進一步生成目標圖像;再次,調整或改變提示文本,以生成新的中間圖像;最終,經過多次重複形成中間圖像的過程,選擇一個滿意的輸出結果。
相較於傳統畫家的“創作”過程,用戶利用Midjourney輸出圖像更類似於一個“試錯”的過程。用戶可能需要向Midjourney提供了“成百上千的描述性提示”,經歷“數百次的中間圖像迭代”才獲得最終結果。既可能帶來超出用戶預期的驚喜,也可能讓用戶最終“失望而歸”。總而言之,由於用戶對Midjourney生成的圖像不具有控制力和預期性,所以無法論證用戶在其中的創造性投入或干預。

(A reproduction of the cover page and the second page of Zarya of the Dawn, from the US Copyright Offices letter. Image: Zarya of the Dawn — Kris Kashtanova / Midjourney)
內在原因:ChatGPT生成內容不構成作品是因為難以證明用戶的創作貢獻
從“Midjourney案”的上述裁定可以得出,美國版權局拒絕對目前ChatGPT類產品生成內容進行版權保護的直接原因是,難以證明“用戶(自然人)對於AIGC模型生成的內容存在創造性的貢獻”。但深層次的原因是,美國立法、司法以及行政機關一直堅守一個基本理念,即只對自然人創作的作品進行保護。“作者”一詞意味着,一件作品要想獲得版權,它必須歸功於人的創作。長期以來,完全由自然界、動物產生的內容素材都不會被認定為版權法上的作品,比如黑猩猩拍照,又如風力侵蝕形成的石像。
美國版權局此前已經多次拒絕將包括AI在內的計算機工具、系統登記為作者,或者將相關生成內容登記為作品。2020年3月30日,美國版權局基於“人類思維和內容創造性呈現之間的聯繫是賦予版權保護的前提”這一基本原則,拒絕了對計算機生成畫作“天堂入口”(A Recent Entrance to Paradise)的版權登記。5原因也是該畫作缺乏賦予版權所需的“人類作者身份”——申請人沒有提供證據證明自然人對該作品有足夠的創造性投入。
實際上,國際保護知識產權協會(AIPPI)在2019年9月18日發布的《關於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版權問題的決議》中也表明了相同的立場。“只有在作品的創作過程中存在自然人的干預貢獻,人工智能生成的內容才有資格構成作品。如果沒有自然人的干預,人工智能生成的內容不應受到版權的保護。”
從我國司法實踐來看,自然人創作也是作品成立的必要條件。在2018年的“菲林訴百度案”中,海淀法院和北京知產法院明確表示涉案分析報告系由“威科先行數據庫”的“可視化”功能自動生成,某種意義上只能認可是“威科先行庫‘創作’了該分析報告”。6由於分析報告不是自然人創作的,因此即使涉案分析報告外在呈現具有客觀上的獨創性,仍不是《著作權法》意義上的作品。
也有觀點指出,“我國和美國在版權領域都存在職務作品或者雇傭作品制度,能否將人工智能生成內容認定為雇傭作品,進而將權利配置給使用人工智能的用戶或公司”。答案是否定的,因為上述觀點實際上“本末倒置”了。雇傭作品或職務作品的制度目的都不是解決特定內容是否構成版權法上的作品,而是對已經構成作品的權利歸屬進行特殊的分配。作品必須首先由自然人創作完成,然後再根據創作的特定目的判斷是否將相關權利賦予其他自然人或者法人、其他組織。
在“天堂入口案”中,申請人Thaler主張,“人工智能可以成為作者,因為雇傭作品原則允許擬制的人(如公司)成為作者”,但美國版權局認為這絕無成立可能。首先,雇傭作品必須是由與公司簽署雇傭協議的自然人完成,或者由一個或多個自然人在單獨的書面協議中明確約定生成的作品是雇傭作品。在這兩種情況下,雇傭作品都是合同約定的結果,但人工智能無法簽訂有約束力的法律合同。其次,雇傭作品規則只涉及作品所有者的認定,而不涉及“特定內容本身是否構成作品、受版權保護”這一前置性問題。

(A Recent Entrance to Paradise, Stephen Thaler/Creativity Machine)
澄清誤區:我國AI版權領域兩個代表性案例並不存在法律論證上的衝突
不同於“菲林訴百度案”,深圳南山法院在2019年審理的“騰訊訴網貸之家案”7中,則認定由“Dreamwriter軟件”輔助創作的財經文章構成《著作權法》上的作品。由此,後續國內很多觀點便認為,我國司法實踐中對於AI生成內容是否構成作品,存在法律認定上的分歧甚至衝突。但實際上,兩地法院的法律論證觀點具有根本上的內在一致性:AI生成內容只有證明存在自然人的獨創性貢獻才會被認定為作品。不同的判決結果歸因於兩個案件涉及的AI模型(或者說機器模型)在運行機制方面存在本質區別。
在“騰訊訴網貸之家案”中,法院明確表示“Dreamwriter軟件”是一種“寫作助手和輔助創作工具”,而在“菲林訴百度案”中法院對威科先行數據庫“可視化報告”功能強調的是“自動生成工具”。是否存在“人類作者”或者“自然人創作貢獻”的“關鍵問題”是,計算機是“僅僅作為一種輔助工具”,還是實際自動“構思並執行了作品中的創作要素”。AI模型軟件“輔助創作”與“自動生成”的差別,實際從根本上決定了用戶對於生成內容是否存在創作貢獻,也即決定了AI生成內容能否構成作品。
在“騰訊訴網貸之家案”中,法院指出涉案文章的表現形式是由,“Dreamwriter軟件”的具體使用者——原告主創團隊人員的個性化安排與選擇所決定的。在涉案文章生成過程中,文章框架模板的選擇和特定用語的設定、數據抓取和填補觸發條件的設定等均由主創團隊相關人員選擇與安排。原告主創團隊的上述選擇與安排屬於與涉案文章的特定表現形式之間具有直接聯繫的智力活動,符合著作權法關於創作的要求。
在“菲林訴百度案”中,法院指出涉案分析報告在軟件開發和軟件使用兩個環節有自然人參與,但都不存在創作性貢獻。軟件開發者沒有根據其需求輸入關鍵詞進行檢索,該分析報告並未傳遞軟件研發者思想、感情的獨創性表達;而軟件用戶僅提交了關鍵詞進行搜索,應用“可視化”功能自動生成的分析報告亦非傳遞軟件用戶思想、感情的獨創性表達。因此,涉案報告未能證明自然人的創作性貢獻於其中,不能構成文字作品。
實際上,3月16日美國版權局新發布的註冊指南也再次明確,AI工具的不同內在機制和原理,決定了生成內容版權屬性的判定。“利用AI工具生成的內容,能否證明存在自然人的創作貢獻,進而判定是否構成作品,答案取決於AI工具生成內容的機制原理,以及AI工具是如何被自然人用來生成最終內容的。”

(圖片源自騰訊-Dreamwriter寫稿機器人宣傳視頻)
問題癥結:混淆AI“自動生成”和“輔助創作”引發國內版權領域的爭議
可以說目前,國內各界對於AI生成物是否構成作品之所以長期存在爭議,很重要的原因在於沒有把討論的前提界定好,把AI自動生成和輔助創作混為一談。實際上,雖然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對於AI生成內容的作品屬性尚無明確認定結論,但在2020年5月29日發布的《經修訂的關於知識產權政策和人工智能問題的議題文件》8中,便已經闡釋自動生成和輔助創作的劃分是解決這個問題的前提。文件表明,“人工智能生成”與“人工智能自動創作”是可以互替使用的術語,系指在沒有人類干預的情況下由人工智能生成產出。要與“人工智能輔助完成的”產出加以區分,後者需要大量人類干預和/或引導。
從國內外案例實踐來看,法院系統和版權行政機關一個相對清晰的共識是,目前ChatGPT這類AI自動生成模型如不能證明自然人的創作性貢獻,則無法將生成內容認定為作品加以保護;而對於AI輔助創作的內容,因為是由自然人主導和控制,具有自然人的創作貢獻則可以被認定為作品。由此關鍵的問題是,在什麼情況下人類參与AI等創作工具生成的內容符合作品保護的法定標準——存在自然人的創作貢獻?
這裏以2014年8月27日,美國版權局裁決的MK公司“絮狀物分析儀樣本圖像(Sample Floc Analyzer Image)”版權註冊案為例。MK公司主張利用“絮狀物分析儀”生成樣品分析圖像的過程,可以比作“人利用相機創作普通攝影作品的過程”:絮狀物分析儀相當於專門設計用來拍攝紙張或其他薄片樣本的特殊相機,這個特殊相機由一系列的軟硬件設備構成。9
美國版權局表示,攝影師可以憑藉對拍攝主題、角度、亮度的選擇以及拍攝時間的瞬間把握,滿足攝影作品獨創性的要求。但本案中,申請人並沒有做出版權法意義上的創造貢獻,只是在實施絮狀物分析儀要求的操作方法:除了將一張紙送入機器並指示程序分析紙張中的絮狀物厚度之外,對於最終輸出的內容沒有任何可歸於自己的創造性貢獻。同時申請人明顯也不存在版權法上的創作初衷,因此其操作絮狀物分析儀生成的內容難以構成版權法上的作品。
新的關注:“prompt”本身的獨創性不影響ChatGPT生成內容的屬性判斷
由此,我們不禁開始反思當用戶以“prompt”提示文本的方式對ChatGPT進行提問或者要求Midjourney輸出一幅圖畫時,可能並不存在創作的目的。此時,用戶更像是利用搜索引擎,檢索自己需要的文字答案或者圖片的行為。毫無疑問,我們不會認為檢索本身是一種創作行為。但當遊戲插畫師利用“photoshop”這類輔助創作軟件進行繪圖時,我們則不會懷疑他們在進行一種美術創作。
這裡有一個新的疑問需要回應——“當用戶提供了足夠具體的‘prompt’時,其對於AI輸出的內容是否便具備創作貢獻,相應的內容也便可以被認定為作品?”實踐中,用戶為了盡可能獲得和預期相一致的文字或圖像,確實可能會向ChatGPT或Midjourney輸入一段經過構思設計的提示文本。但實際上,不論“prompt”多具體,即便“prompt”本身可能構成文字作品,也無法改變目前ChatGPT類產品作為AI“自動生成”而非“輔助創作”的本質,因為用戶本質上仍無法直接控制和準確預見輸出的內容。
例如,在前述“Midjourney案”中,美國版權局否定了申請人的抗辯,即AI生成圖像是“自然人撰寫的獨創性提示文本的外在視覺呈現”。美國版權局指出,雖然存在將申請人“prompt”本身註冊為文字作品的可能。但對於Midjourney輸出內容而言,並不能保證申請人特定“prompt”會產生與之直接對應的視覺呈現。相反,申請人輸入“prompt”的行為更接近於一種建議,類似於客戶委託藝術家創作圖像的情形。
假設申請人委託一位漫畫家創作一幅圖像,要求包含“一位名叫Raya的老年白人婦女”,“Raya有一頭捲髮,她坐在一艘宇宙飛船內”,並指示該圖像具有“星際迷航”的畫風。當漫畫家按照上述要求完成圖像后,相信沒有人會認為是申請人創作了這幅圖像,雖然她提出了明確的圖像內容要求。當然該圖像可以成為雇傭作品,但實際創作者無疑是收到申請人指示並決定如何具體創作這些元素要求的漫畫家。
同理,如果申請人在谷歌中輸入這些搜索指示,也不能聲稱根據她“檢索關鍵詞”獲得的圖像是由其“創作”的,無論最終谷歌展示的結果圖像與她的內容描述多麼契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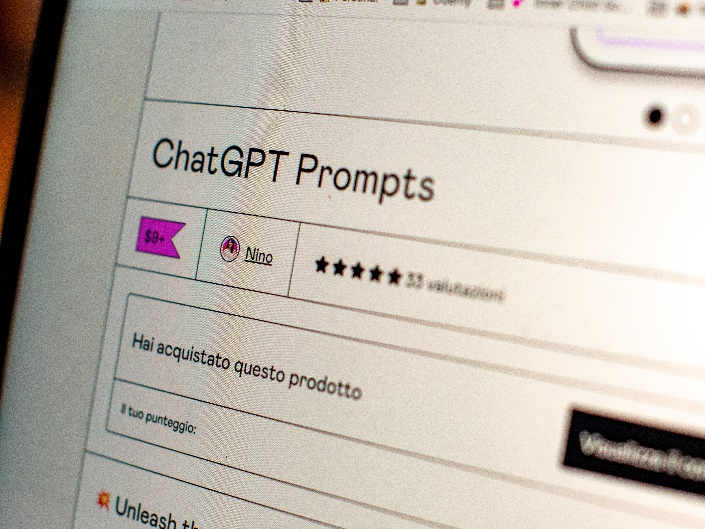
法律定位:如何在著作權制度下對於ChatGPT生成內容加以保護?
從著作權制度視角看,可以探索對AI“輔助創作”和“自動生成”的內容進行二分保護。Dreamwriter等AI輔助創作工具,在法律認定層面和傳統的創作工具相同:由自然人控制,輸出包含自然人創作貢獻的內容;只要生成的內容符合特定作品的形式要求,便可以被認定為文字、美術、視聽等作品。而ChatGPT、Midjourney等AI自動生成工具,通過用戶輸入“prompt”生成特定內容,因為缺乏自然人的獨創性貢獻,實際上難以滿足《著作權法》對於作品的要求。
但這並不意味着著作權制度,無法為ChatGPT類產品的生成內容提供保護。作為大陸法系國家,我國採用廣義的著作權制度,除作品之外還對“鄰接權內容”加以保護,比如錄音錄像製品、廣播電視節目等。鄰接權不要求權利人對生成的內容付出創作性貢獻,而是強調在內容形成的過程中權利人是否有相關投入(包括勞動、金錢和時間等),這便契合了目前ChatGPT類產品生成內容的客觀屬性。對於ChatGPT類產品的輸出內容而言,用戶雖然沒有創作性貢獻,但無疑存在實質性的投入,比如花費大量時間構思輸入“prompt”,又比如特定產品和服務使用費的支出。
而作為“普通法系國家”的美國,在版權法中僅僅存在作品制度而不存在鄰接權制度,即僅對“存在自然人創作性貢獻的內容”加以保護。美國最高法院多次表示,作為一個憲法問題,版權只保護那些超過最低限度創造性的作品。如果內容中“完全缺乏創造性的火花,或輕微到不存在的程度”,就不能獲得版權法的保護。
在“Midjourney案”中,美國版權局表示並不質疑申請人花了大量時間和精力使用Midjourney生成圖像,但這種付出並不意味着申請人存在版權法下的創作性貢獻。美國法院早已明確拒絕“額頭流汗原則”可以作為版權保護的基礎。美國版權局也表示“不會考慮創作所需的時間、精力或費用”,因為這些因素“對特定內容是否具備版權法和憲法所要求的‘最低限度的創造性’沒有關係”。
因此,相較於美國,我國著作權制度對於AI自動生成內容的保護存在天然的優勢。後續可以在修法過程中嘗試論證,ChatGPT類產品生成內容鄰接權保護模式的合理性與可行性。此外,當ChatGPT類產品生成內容在涉及B端企業用戶和市場經營競爭時,能否通過《反不正當競爭法》“一般條款”涉及的“競爭利益”加以保護,也值得思考,雖然可能存在更嚴格的適用限制。
值得關注,英國早在《1988年版權、設計和專利法案》修訂中,便已經對“計算機生成作品”(Computer-Generated Works)作出了規定,且目前看可以適用於AI自動生成內容的保護。該法案第9、12、79、178條做出了相應規定:“計算機生成作品是指沒有人類作者的情形下,由計算機生成的作品”;“計算機生成作品的作者是操作必要程序,使作品得以產生的自然人”;“計算機生成作品的保護期限為50年”;“作者的精神權利不適用於計算機生成作品”

權利分配:域外實踐與既有判決傾向將AI生成內容權利配置給用戶
對於AI生成內容的歸屬問題,如果是AI輔助創作,使用人享有相關的權利應屬無疑。對於ChatGPT等AI自動生成內容,從國外ChatGPT類產品的用戶協議來看,大多數平台會通過合同約定將AI自動生成內容的權利配置給用戶。例如OpenAI公司用戶協議規定,“ChatGPT輸出內容的相關權利歸屬於用戶,用戶在遵守服務條款后,可以出於任何目的使用輸出內容”。Midjourney在用戶協議也約定,“用戶對於使用服務生成的內容享有所有權,只要不違反現行法律的要求。”
但也有例外規定,比如Stable Diffusion Online則表示生成的內容將適用“CC0 1.0 通用協議”,即將生成內容投入“公有領域”,任何人都可以通過複製、修改、發行等方式利用,包括商業目的,無需獲得事前授權。
從國內司法實踐來看,在“菲林訴百度案”中法院傾向於將AI(機器)自動生成內容的相關權利分配給最終使用者。判決表示對於軟件研發者來說,其利益可通過收取軟件使用費用等方式獲得,已經得到回報;且分析報告系軟件使用者根據不同的使用需求、檢索設置而產生的,軟件研發者對其缺乏傳播動力。軟件使用者則通過付費使用進行了投入,基於自身需求設置關鍵詞並生成了分析報告,並具有進一步使用軟件以及傳播分析報告的動力和預期。因此,從激勵軟件使用和內容傳播角度,應當將分析報告的權益賦予用戶。
著作權作為私有權利,在不違背法律規定的情況下,當事人可以自由約定內容的權利歸屬。而上述判決,從“最密切原則”——相關主體和生成內容的直接關聯程度,“額頭流汗原則”——相關主體對於生成內容的付出回報機制,“著作權制度初衷”——如何最大程度促進內容傳播、公眾內容的獲取等角度考量,實質上更傾向於將ChatGPT等AI自動生成內容的原始權利配置給最終使用者。

權責一致:ChatGPT類產品生成內容版權侵權的三方責任承擔機制
目前ChatGPT類產品生成內容主要涉及三方主體:AIGC模型的研發者、AIGC模型的商業化應用者,以及最終使用AIGC模型生成內容的用戶。這裏我們首先需要明確的是,從技術角度看,當用戶輸入一段提示詞,AI模型隨機輸出相應的文字或者圖片,存在一定的侵權概率。此前有國外研究團隊層指出:利用Stable Diffusion模型生成的內容與數據集作品相似度超過50%的可能性為1.88%。但對於輸出內容是否實際侵權,述三方主體都不存在明確的預期,因為這一過程具有很大的隨機性和不確定性。
根據“權利之所在,責任之所在”的基本原則,誰最終享有ChatGPT類產品生成內容的權利(不論是著作權亦或是鄰接權等),誰便需要承擔生成內容可能引發的版權侵權責任。如果約定由AIGC商業化應用平台享有生成內容的相關權利,平台需要承擔直接的版權侵權責任;如果由用戶享有生成內容的相關權利,用戶則需要承擔直接的版權侵權責任。從目前域外ChatGPT類產品平台用戶協議可以看出,其在將內容權益配置給用戶的同時,也均會明確表示用戶對輸出的內容承擔全部的法律責任。
這裏需要討論的是,即使用戶承擔AI生成內容的直接侵權責任,AI模型的商業化應用者應當承擔何種程度的責任?應當說,從ChatGPT類產品的實際運營來看,AI模型的商業化應用平台類似於一個新的網絡服務類型。例如有觀點便認為ChatGPT像是一個全新的搜索服務工具。因此,是否應當從版權保護注意義務的角度,為其匹配一個新的“避風港”責任機制,如同當年美國《数字千年版權法》設立的四種服務類型責任豁免制度一般,這值得思考。例如,如果ChatGPT類產品的商業化應用者盡到“侵權避免提示”“通知處理”等義務后,是否便可以豁免相應的間接侵權責任。
進一步思考,AI模型研發者對於生成內容涉及的侵權問題,是否需要承擔責任?從侵權行為可預見性、侵權行為控制力以及侵權直接獲益等角度評估,模型研發者相較於模型商業應用者和用戶而言,與輸出侵權內容的關聯度更低、控制力更弱、經濟利益更少。實際上,上游的AI模型本身或者相應的API接口作為一種通用技術或者服務,符合知識產權法中的“技術中立原則”或者說“實質性非侵權用途”:因為輸出的內容具有不確定性,既可能侵權(小概率事件),更可能不侵權(大概率事件);並且對於下游模型商業應用者和最終用戶的使用行為不具有實際的控制能力。因此,AI模型研發主體原則上無需對生成內容涉及的侵權問題擔責。
未來展望:ChatGPT類產品為內容創作領域人機協作範式奠定了重要基礎
目前,AIGC正越來越多地適用於数字內容領域的創意性生成工作——在文學、繪畫、影視等領域釋放技術帶來的新價值。在人機協作新範式之下,也需要我們不斷思考所面臨的版權新問題。

現實中,對於“ChatGPT生成文字”或者“Midjourney生成圖片”,創作者們一方面可能會對其進行“改編”,增加包含自身獨創性貢獻的內容,進而形成了新的“改編作品”;另一方面也可能會對其進行“彙編”,在內容的選擇或者編排上體現獨創性,進而形成新的“彙編作品”。那麼如何對上述新形成的內容進行屬性認定?又該如何從權利角度保障創作者們的價值貢獻值得思考。
未來,伴隨ChatGPT類產品技術的持續發展完善,人機協作範式可能會成為內容創作領域的常態化實踐。雖然從目前國內外案例來看,ChatGPT類產品輸出的內容本身很難被直接認定為作品,但並不意味着人機協作下完成的內容在整體上無法受到版權法保護。
一方面,包含ChatGPT類產品生成材料的內容,若能夠體現人類獨創性的貢獻,那麼整體上便可以構成版權法上的作品;另一方面,版權法將只保護上述作品中人類創作的部分,並且這些部分“獨立於”且“不影響”AI生成材料本身的法律屬性判斷。
上述思路源於美國版權局在2023年3月16日的最新指南,同時強調:“若希望註冊包含ChatGPT類產品生成內容的作品,申請人不僅需要論證自身在整體作品中的創作性貢獻,還需要標明作品中哪些內容(部分)是由人工智能所生成的,以備進一步的審核。”
本文內容僅代表作者個人研究觀點
參考資料來源:
[1]Copyright Registration Guidance: Works Containing Material Generat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23/03/16/2023-05321/copyright-registration-guidance-works-containing-material-generated-by-artificial-intelligence.
[2]https://copyright.gov/docs/zarya-of-the-dawn.pdf
[3]ChatGPT類產品最終生成的內容形式各異,涵蓋文字、圖像、語音、視頻等,但內容生成的機制相同:用戶根據自身需求,向ChatGPT或Midjourney的用戶界面輸入描述性的文本提示“prompt”,AI生成模型在對文本進行解碼之後,匹配出此前數據訓練階段與之最相關的內容結果,然後進行對外輸出.
[4]Based on the Office’s understanding of the generative AI technologies currently available, users do not exercise ultimate creative control over how such systems interpret prompts and generate material.
[5]https://www.copyright.gov/rulings-filings/review-board/docs/a-recent-entrance-to-paradise.pdf
[6]2018)京0491民初239號;(2019)京73民終2030號.
[7](2019)粵0305民初14010號.
[8]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499504.
[9]https://www.copyright.gov/rulings-filings/review-board/docs/2014-appeal-SampleFlocAnalyzerImage2014.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