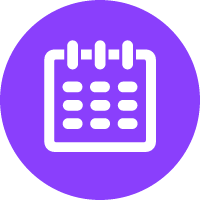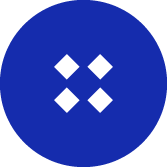所有語言
分享
為什麼IBM的市值只有微軟的十六分之一?
我平時的一個主要學習方式(以及愛好)是讀財報。
上市公司每個季度的財報披露,包括公告、新聞稿和分析師電話會議紀要,向我們提供了大量的財務信息和業務信息,是一個不容忽視的知識寶庫。最近兩年,因為港股和中概股實在沒法看,我的大部分時間花在讀美股科技股財報上——包括微軟、蘋果、英偉達等市值最大的公司,也包括IBM這樣在某些垂類具備巨大影響力的公司。
在我讀中學的時候(也就是第一次納斯達克泡沫破裂前後),IBM是與微軟並列的科技巨頭之一,雖然其市值已經低於後者,但仍處於一個重量級。此後二十年,IBM經過了多次業務重組,確立了以企業級軟件為核心的商業模式,同時也退出了“科技巨頭”的行列,與微軟等一線科技公司的差距越拉越大。此時此刻(2024年9月11日):
IBM的市值只有微軟的1/16,更準確的說是6.14%;上個季度IBM的營業收入只有微軟的1/4,凈利潤只有微軟的1/12;Non-GAAP凈利潤也只有微軟的1/10;
在規模遠遠小於微軟的情況下,上個季度IBM的營業收入同比增速僅有2%,而微軟為15%;IBM的凈利潤增速倒是略快於微軟(14% vs. 10%)。
有必要指出,上述對比不完全公平,因為2021年IBM剛剛完成了對IT基礎設施運維業務的拆分,後者變成了一家名為Kyndryl(勤達睿)的獨立上市公司。然而,就算把Kyndryl加進來,IBM的營業收入也僅能達到微軟的30%。何況Kyndryl被拆分的原因就是其利潤過於微薄,不太受資本市場歡迎,目前其市值僅有約50億美元(相當於1/600個微軟)。
在這個生成式AI驅動的時代,微軟的戰略地位遠比IBM更好:前者是OpenAI最大的外部投資者,旗下的Azure雲是AI訓練最常用的雲,而且已經在Office, Teams, Bing等軟件和服務當中全面融入了GPT;後者則淪為一個不太重要的角色,以IBM Watson為代表的昔日榮光早已褪色,現在的IBM只能勉強排進AI技術的第二集團。在可見的未來,微軟和IBM的差距繼續拉大的可能性,顯然遠遠高於拉近的可能性。
01
那麼問題來了:IBM是怎麼淪落到這個地步的?
要知道,整整十二年前,也就是2012年9月11日,微軟和IBM的差距還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在那一天,IBM的市值為2334億美元,微軟的市值為2568億美元,兩者完全就是一個量級的公司。
在那個季度(即2012年7-9月),IBM的營業收入為247億美元,微軟為160億美元;IBM的凈利潤為38億美元,微軟為45億美元;兩者仍然是一個量級的公司。
此後十二年當中,微軟的市值增長了近12倍,而IBM的市值(已經考慮到拆分因素)原地踏步;兩者市值被拉開的差距,幾乎與凈利潤被拉開的差距相同,說明這一變化是基本面驅動的,而非市場一時頭腦發熱。
耐人尋味的是,這十二年當中,兩家公司的管理層都是相對穩定的:從2012年至2020年,IBM由羅睿蘭(Ginni Rometty)擔任CEO,直至2021年由阿溫德·克里希納(Arvind Krishna)取而代之;而從2014年至今,微軟一直由薩特亞·納德拉(Satya Nadella)擔任CEO。所以這個問題很大程度上可以簡化為:羅睿蘭主政期間的IBM,與納德拉主政期間的微軟相比,犯下了什麼錯誤?或者說,未能做出什麼正確的事情?
原因肯定很多。我既沒有擔任過跨國公司CEO,也沒有從事過技術工作,所以只能從旁觀者的視角,大致說一下自己的看法。從事後諸葛亮的角度看,IBM至少在以下三個重大方向上犯了錯誤,其重要程度依次遞減:
- 沒有即時下注云計算尤其是公有雲業務,從而未能適應IT服務“雲端化”的趨勢;
- 沒有追上AI技術向深度學習轉變的浪潮,從而使自己過去幾十年的AI技術積累迅速過時;
- 沒有押注於任何消費端(To C)業務,從而失去了更多可能性(雖然押注了也未必有用)。
先說第一條。過去二十年,全球IT服務最重要的趨勢就是雲計算:從以前的企業自建IT系統,逐漸轉變為對外採購公有雲平台的服務,由此實現IT基礎設施乃至軟件服務的全面“雲端化”(也就是“外包化”)。第一個吃螃蟹的是亞馬遜,AWS已經成長為其最賺錢的業務(遠比主營的電商業務更賺錢);其次就是微軟。早在接任微軟CEO之前,納德拉就是微軟向雲計算轉型的重要人物,一手促進了微軟數據庫、Windows服務器和開發工具業務與Azure雲平台的融合。在接任CEO之後,納德拉堅決地、毫不猶豫地對Azure加大投入,終於使得後者成為了微軟的收入增長引擎以及最大的單一收入部門。
事實上,從技術和產品的視角看,雲計算與微軟原有業務的相關性有限:微軟在傳統PC和服務器軟件上的優勢,並不能直接轉化為雲計算服務上的優勢,前者的“雲端化”是一個漫長而痛苦的過程。所謂“微軟傳統業務與雲計算業務的協同性”,主要是指銷售端的協同性——微軟的銷售體系(包括直銷人員和經銷商)覆蓋了大批企業,可以向這些企業推薦Azure雲服務;微軟的老客戶採購Azure也可以拿到一定的折扣。這種基於銷售端的“優勢”,IBM同樣具備,甚至Oracle也具備,只是其銷售覆蓋面有所不同而已。
簡而言之:微軟在舊時代的技術積累,並不能保證它的Azure在新時代能追上如日中天的亞馬遜AWS。AWS的前身早在2002年就成立了,2006年就開始對外全面提供服務;Azure的前身則在2008年才成立,2010年才開始對外提供服務。對於技術進步日新月異的雲計算行業來說,4-6年的差距是非常巨大的,必須加倍努力才有可能扳回來。納德拉執掌微軟雲業務之時,其實已經是向雲計算全面轉型的最後時間窗口了;如果再晚兩年,Azure恐怕就要落後於更後起的谷歌雲了!納德拉的"all-in Azure"決策的戰略意義之大,怎麼估計都不過分!
而IBM在雲計算領域的落後,幾乎完全可以歸結為“動手太晚”。2010年,IBM才開始探索雲計算業務;2013年,才通過收購SoftLayer,建立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雲服務部門。然而,直到2017年,IBM才確立了以“混合雲”(Hybrid Cloud, 可以視為公有雲和私有雲的結合體)為主的雲服務戰略,並且在2018年通過收購Red Hat強化了這個戰略。彼時彼刻,亞馬遜AWS、微軟Azure、谷歌GCP三強鼎立的形勢已經形成,留給IBM的市場空間已經非常狹小,主要局限於那些偏好混合雲的大型企業客戶。
搞笑的是,按照IBM官方的說法,羅睿蘭擔任CEO期間最大的功績是“確立了IBM的混合雲戰略”——這話當然不錯,只可惜這個戰略本應在2012-2013年就確立,而不是等到2017-2018年!“遲到的正義為非正義”,同理,遲到的正確決策只能淪為平庸的決策。況且混合雲並非什麼IBM獨家技術,亞馬遜、微軟、谷歌乃至Oracle都可以做;哪怕退回這個狹窄的垂類市場,IBM的地位仍然不夠穩固。
繼續說第二條。IBM曾經在AI技術領域維持了長達五十年的領先地位,70后至80后的朋友應該都對1996年“深藍”擊敗卡斯帕羅夫之戰記憶猶新;美國人可能還對IBM Watson於2011年在《危機邊緣》(Jeopardy!)知識競賽當中擊敗人類选手留下了深刻印象。羅睿蘭擔任CEO期間的一個重要戰略,就是通過Watson解決方案,把IBM的AI技術進行商業變現,其首選對象是醫療行業。
事實證明,歐美醫療行業過於複雜,涉及的監管和倫理問題太多,至少在當時並不十分適合由AI去改造,所以Watson的商業表現高開低走。但是更重要的是,2012-2013年(也就是Watson開始大規模商用的時間節點)發生了一場AI技術革命:基於神經網絡的深度學習技術不僅取代了傳統的知識圖譜(符號主義),也取代了統計學習等傳統機器學習技術,成為最高效、應用範圍最廣泛的AI基礎技術。此後短短十年間,深度學習徹底改造了互聯網內容分發和廣告推送體系,開啟了自動駕駛和大語言模型(LLM)等新興產業,在學術界也成為了絕對的主流。

作為老牌AI技術霸主,IBM未能跟上時代;至於原因究竟是管理層決策失誤、投入資源不夠還是執行效率低下,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當谷歌以一年10家的速度收購基於深度學習的AI創業公司、以天價延攬包括伊利亞·蘇茨克維(Ilya Sutskever)、吳恩達在內的頂尖AI科學家時,IBM的動作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結果就是,在短短2-3年之內,谷歌奪走了AI技術霸主的地位,並且迅速將AI應用於搜索引擎、翻譯等服務上,從而讓“技術-應用-商業化”的飛輪轉動了起來。可憐的IBM則直到2021年才承認Watson的失敗,當時它的AI基礎研發實力不但早已被谷歌甩出了好幾個身位,而且已經落後於亞馬遜、Meta。
嚴格地說,微軟在這一局裡也是後來者,深度學習技術從來不是它的強項。但是微軟做出了一個相當正確的決定,就是在2019年投資OpenAI,並且將後者的服務融入Azure雲平台。ChatGPT橫空出世之後,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認,這是微軟歷史上最重要、最成功的一次戰略投資。與GPT的深度合作不僅拉動了微軟Office, Teams等軟件服務的銷量,更重要的是確立了Azure的“AI服務第一雲平台”的地位——從2023年開始,AI需求每個季度都能至少把Azure的收入增速拉高5個百分點。現在輪到亞馬遜感受到危機、急忙尋找各種應對手段了!
當然,微軟並沒有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對外投資上,它對於生成式AI的內部研發一直在進行中。例如,它曾與英偉達共同開發了萬億參數規模的Megatron大模型,而且至今仍在開發和迭代大模型。最近五年,由於Azure逐漸釋放出巨大的盈利能力和現金流,微軟得以向生成式AI等基礎研發方向分配更豐厚的資源,實現成熟業務對新興業務的“供養”;而IBM或Oracle則沒有這麼多資源可供揮霍。成功能夠帶來成功,就像錢能生錢,關鍵在於資源分配的方法得當。
最後說第三條。自從2005年向聯想出售PC業務之後,IBM幾乎就沒有像樣的消費端業務了。此後近二十年時間里,IBM對消費端業務沒有展現過任何興趣,不管是消費互聯網、消費硬件還是內容服務。公允地說,這不能算一個真正的“錯誤”,因為IBM確實不具備消費端業務的基因,就算過去十多年裡它押注了什麼消費業務,我們也很難預測它取得多大的戰果。
問題在於,同一時期的微軟也不具備太多的消費端業務基因,但它還是屢敗屢戰、愈戰愈勇,頑強地堅持了下來。對遊戲業務的投入,貫穿了比爾·蓋茨、史蒂夫·巴爾默和薩特亞·納德拉三位CEO的任期;對智能硬件的投入,雖然在智能手機領域輸的一塌糊塗,但是在平板電腦取得了一定的戰果,維持了微軟的戰略性存在;對消費互聯網的投入,主要是Bing搜索引擎和LinkedIn,總體看來是成功的,尤其是在與生成式AI融合之後,其戰略價值正在上升。附帶說一句,Bing的啟動和LinkedIn的收購,都發生於納德拉的CEO任期內。
我們不難發現,巴爾默擔任CEO期間,微軟確實不擅長消費端業務,朝令夕改、毫無頭緒,收購過來的優質業務往往也灰頭土臉收場。可是在納德拉接手之後,微軟的消費端業務更成熟了,其表現至少可以稱之為中規中矩。從財務角度看,時至今日,微軟的全部消費端業務均實現了盈虧平衡,就連歷史上的燒錢大戶遊戲業務也是如此(這得益於對Xbox硬件平台定位的轉變)。從資本市場的角度看,它們不再是拖後腿的業務,對微軟市值的正面貢獻越來越明顯了。
納德拉對於消費端業務的態度,集中體現在2022年初他對收購動視暴雪決策的解釋當中:對於遊戲這樣一個擁有超過30億用戶的大型消費業務,微軟不能缺席。同理可以推斷出,在納德拉看來,微軟若想保持科技巨頭的地位,就不能龜縮在企業級業務的“舒適圈”里,必須打出去。這一方面是為了建立與消費者的直接聯繫、培養用戶心智,另一方面是為了形成業務協同效應——例如AI與Bing的協同效應,以及Azure與雲遊戲的協同效應。反觀IBM,過去二十年的歷任CEO,沒有一個做出過類似的判斷;他們無一例外地認為,IBM可以通過僅僅做企業級業務,甚至僅僅做利潤豐厚的大企業業務,就維持科技巨頭的地位。歷史證明他們錯了。
不過,既然IBM已經在雲計算、AI兩個戰略方向上犯下了更不可饒恕的錯誤,對消費端業務毫無押注的錯誤就沒那麼重要了,甚至可以忽略不計。諷刺的是,IBM歷史上最高光的時刻,恰恰是它在消費端最強大的時刻——從1980年代直至1990年代初,IBM PC引領了第一波信息技術革命走進千家萬戶,直到康柏、惠普、戴爾等生機勃勃的新廠商後來居上。在消費端電腦市場,蘋果曾經是IBM的手下敗將,可是在短短十幾年內它就重新站了起來,成為了一家完全立足於消費端市場的科技巨頭。世事萬變,但是事在人為,“基因”也好、“歷史積累”也好,歸根結底是依靠人去執行的。
02
因此,我們更能理解,在美式上市公司中,CEO為什麼總能拿到極端豐厚的薪酬了:
根據彭博新聞的統計,2022年美國上市公司CEO的平均薪酬是員工平均水平的400倍!像埃隆·馬斯克這樣的明星CEO,每年能夠拿走價值幾十億美元的薪酬包。納德拉2023年的薪酬包為4850萬美元;而在他就任CEO之前的2013年,作為微軟高級副總裁、雲計算業務的負責人,他的薪酬包僅為760萬美元。
哪怕考慮到最近十年的通貨膨脹因素,差距也是十分巨大的!
這種情況合理嗎?考慮到CEO至關重要的地位,顯然是合理的。在納德拉擔任微軟CEO的十年之內,微軟的股價上漲了10倍;而在此前巴爾默的任期內則基本是零增長。如果羅睿蘭在擔任IBM CEO期間能夠在雲計算和AI兩大戰略性問題上面至少做出一個正確決策,並執行下去,那麼IBM現在可能還屹立於科技巨頭之林,其市值可能是萬億美元而不是1850億美元。美式公司治理結構賦予了CEO幾乎無限的業務決策權,所以CEO應該為一切錯誤承擔責任,也應該為一切成就獲得獎勵。所謂“權力與義務的統一”,就是這樣的。
由此可以進一步推斷出:在採用美式公司治理結構的中國公司,主要是互聯網中概公司當中,CEO的權力和責任就更大了。他們不但享有美式公司所賦予的制度性權力,還擁有中式人情社會所特有的非制度性權力,從而可以更高效、更徹底地將自身意志貫徹下去。當他們做出正確或錯誤選擇時,對公司的影響就更大了。所以說,互聯網大廠的成敗至少有一半可以歸結為一號位的問題,這個說法或許有些偏激,但還是有道理的。
就上面這個問題,我還想展開說更多,但那應該是另一篇文章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