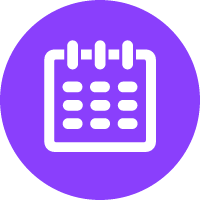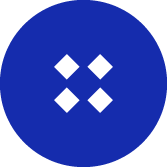所有語言
分享
DeSci:科學資助的革新之路
作者:Nadia Asparouhova 編譯:LlamaC

(作品集:Burning Man 2016,關於 Tomo:eth 基金會插畫師)
對於那些處於科學和技術之間的人來說,很難不注意到過去兩年裡出現的大量新計劃,這些計劃旨在特別改善生命科學領域。
雖然我沒有科學背景,也與這個領域沒有任何個人關係(除了認識並喜歡許多參与其中的人),但我開始對了解這個領域為何突然發生變化感興趣,特別是從慈善的角度來看。弄清楚在科學領域什麼是有效的,可以幫助我們解決世界上其他類似形狀的問題。
為了理解發生了什麼,我查看了過去十年(大約 2011-2021 年)科技領域中與科學相關的努力的例子。我尋找能幫助我推斷當時的規範和價值觀的模式,以及改變這些態度的轉折點。我還採訪了該領域的許多人,以幫助我填補空白,並了解他們的價值觀以及成功的樣子。
一個警告:對於「為什麼這種文化發生變化」這樣的複雜問題,很少能夠,甚至不可能產生清晰的答案,所以請將這篇文章視為進一步研究的起點。
科學中的問題
當人們說他們想「更好地做科學」時,他們試圖解決哪些問題,以及如何解決?
在科學領域工作和周圍的人似乎普遍認識到幾個觀察結果。這些主題在其他地方已經得到了廣泛和更詳細的討論,所以我只會簡單地提及它們:
作為一名科學家,獲得資金的過程緩慢且官僚化
Fast Grants(一個為應對 COVID-19 疫情而啟動的快速撥款項目)的受歡迎程度說明了科學家缺乏選擇。其創始人在回顧中指出,他們對來自排名前二十的研究機構的申請者數量感到驚訝:「我們沒想到頂尖大學的人在疫情期間會在資金方面如此掙扎。」然而,在發送給撥款接受者的調查中,64% 的受訪者表示,如果沒有 Fast Grant,他們的工作根本不可能進行。
學術界的獎勵體系雖然健全,但並不能選出最佳的工作
科學家們被期望在期刊上發表他們的研究成果,他們的聲譽可以通過引用次數來衡量。但同行評審傾向於選擇共識而非冒險,科學家們感到壓力要追求數量而非質量,此外還有許多其他問題。
早期職業科學家處於不利地位
科學正在趨向年長和有經驗的科學家。大多數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資助都給予年長的科學家,而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獎的發現年齡也在增加。
定義變革理論
為什麼這些問題重要?如果我們必須為上述觀察結果提出一個「所以呢」的問題,我們可能會說,由於這些系統性挑戰,科學進步並不像它本可以那樣強勁。與其他歷史時期相比,如維多利亞時代或冷戰時期,如今有前途、有才華的科學家似乎很難追求他們的工作,特別是當他們的想法是實驗性的或未經證實的。
New Science 創始人 Alexey Guzey 在 2019 年對生命科學的調查中指出,科學家們已經學會通過一些方法來解決這些問題,例如,申請他們「無聊」想法的資助,然後將其中一部分用於資助他們「實驗性」的想法。無論如何,可以合理假設,如果科學家們不必進行這種周旋,可能會完成更多的工作。例如,從前述 Fast Grants 調查中,78% 的受訪者表示,如果他們能獲得「無限制、永久性的資金」,他們會「大幅」改變他們的研究計劃。
如果我們必須為科學寫一個帶有科技風味的變革理論,那麼它可能看起來像這樣:
通過消除世界頂尖科學家面臨的財務和制度障礙,確保科學進步能夠蓬勃發展,使他們能夠充分追隨自己的好奇心,併產生能夠應用於造福人類的研究成果。
在這個聲明中,從業者之間對於他們認為最重要的活動存在分歧:
-
我交談過的一些人認為,科研資金不足或資金流程緩慢是影響最大的槓桿:給科學家錢,讓他們自由發揮他們的想法。
-
其他人認為學術規範是更大的障礙:研究應該更像創業文化那樣運作。
-
還有一些人認為,專註於基礎研究的人與那些希望應用研究成果的人之間存在分歧:後者希望更快地將研究成果推向市場,使人類能夠從科學家的工作中受益。
我將在接下來的章節中更詳細地介紹其中一些方法。
科學也可以被視為一個更廣泛問題陳述的子集:「我們如何支持科技領域的研究文化?」例如,人工智能就屬於這個範疇,但具有不同的發展軌跡和資金歷史。人機交互(HCI)和「思考工具」也是如此。甚至「科學」本身就是一個極其廣泛的類別,正如我們將在接下來的章節中看到的那樣(請注意,特別關注改進科學過程有時被稱為「元科學」)。
在這個案例研究中,我只關注過去十年科學研究與科技的重疊部分。然而,在許多情況下,科技對研究的態度也影響着我們對科學的看法,反之亦然,我會在這裏偶爾提及這一點。
現在我已經把那些注意事項說清楚了,讓我們來看看當今從業者有什麼共同點。回顧上面的變革理論,科技原生方法對科學有什麼不尋常或重要的地方?
對我來說,一個突出的方面是對支持和吸引頂尖科學人才的關注。這裡有一個潛在的假設,即個別科學家的質量很重要,甚至可能是科學的飛躍進步要歸功於少數天才的貢獻,而不是整個科學界。(José Luis Ricón 的一項元分析似乎支持這一假設,儘管他指出這些結論可能因領域而異。)
對「頂尖人才」的關注對我來說感覺非常科技化,類似於創始人對待初創公司的思維方式。雖然沒有完美的精英制度,但科技文化之所以蓬勃發展,部分原因是公司傾向於不太重視出身或工作年限等標誌,而更注重一個人實際完成的成果。優先考慮高質量人才也有助於組織在成長過程中避免衰退。因此,科技界將這種思維方式應用到科學領域並不令人意外。
其次,始終強調產出,特別是將研究成果推向市場。再次,這種「注重結果」的方法對我來說感覺非常符合科技行業的特性:認為基礎研究最終應該服務於一個長期目標,以造福人類——而且我們應該盡可能縮短這個時間線。
我交談過的大多數人認為,如果你能將你的工作商業化,你就應該這麼做——當然,前提是並非所有東西都能商業化。即使是非營利的科學項目也傾向於強調一些受創業啟發的價值觀,比如速度、證明能力和協作。
最後,當今從業者中普遍存在一種隱含的信念,即變革是外生的:我們必須在機構之外工作,從外部施加影響,以實現這些目標。雖然一些組織確實與大學合作,但它們仍然在傳統學術職業道路之外運作。
這些價值觀對於在科技領域工作的人來說可能看起來很明顯,但如果我們回到「確保科學進步能夠蓬勃發展」這一高層願景,應用這些價值觀會排除一些非科技從業者可能會追求的選項:例如,建立博士後項目、改善大學研究實驗室的工具、增加 STEM 研究生項目的招生等。
考慮到這些價值觀,讓我們來看看過去十年科技領域的科研資金是如何演變的。
通過初創企業推動科技創新(2011-2014)
我從對話中聽到的一個共同主題是,過去十年裡科學問題陳述並沒有顯著改變。長期以來,人們普遍意識到科學運作效果不如預期,並希望採取行動改變這一狀況。然而,對於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的看法卻發生了變化。
十年前,大多數人認為創業公司是推動科學進步的最佳方式:要麼創辦公司,要麼為公司提供資金。
當時,經濟學家和作家泰勒·科文(Tyler Cowen)2011 年出版的《大停滯》(The Great Stagnation)一書為科學進步提供了哲學基礎。科文提出了關於美國經濟停滯的更廣泛論點,但他指出科學突破的缺乏和技術進步速度的普遍放緩是其原因之一。
考恩將這本書獻給彼得·蒂爾,後者曾公開談論科技創新的衰退。在《大停滯》中,考恩引用了蒂爾的一次採訪,他表示:「製藥、機器人、人工智能、納米技術——所有這些領域的進展都比人們想象的要有限得多。問題是為什麼。」
大約在 2011 年這個時候,泰爾還為他在 2005 年創立的風險投資公司 Founders Fund 採用了現在臭名昭著的標語:「我們被承諾會有飛行汽車,結果我們得到了 140 個字符。」泰爾決定將這一說法轉化為投資理念,揭示了他的變革理論:科學進步將通過市場來解決,而不是通過資助基礎研究。
雖然很難確定為什麼創業公司在當時成為科學領域的首選方式,但最簡單的解釋是,這與 2010 年代創業公司的普遍流行相關。Y Combinator 這個加速器在使創業變得更具吸引力和更容易開始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它成立於 2005 年,但在 2010 年代達到了文化巔峰。它最成功的校友中有許多來自於 2010 年代創立或實現突破性增長的公司。Marc Andreessen 2011 年的評論文章「軟件正在吞噬世界」捕捉到了當時的情緒:軟件驅動的創業公司可以應用於解決跨行業的許多不同問題。
除了 Breakout Labs(雖然是一個資助項目,但被構建為一個循環基金,收入來自受資助者的知識產權和 / 或版稅)之外,當時著名的科學項目通常是初創公司或風險投資基金。例子包括:

在創業公司之外,當時科技領域有兩個著名的研究贊助者,他們與科學更為接近,但也能告訴我們當時人們如何看待研究:
Google X:Google X 於 2010 年悄然成立,《紐約時報》首次披露了其存在,將其描述為 Google 內部一個專註於「瞄準星辰大海的想法」的秘密實驗室。Google X popularized popularized 了「登月計劃」(moonshots)這個術語,現在將自己描述為「登月計劃工廠」。
MIT 媒體實驗室:MIT 媒體實驗室現在將自己描述為「跨學科研究實驗室」。雖然不專註於科學,但它經常被引用為科技與學術研究文化的象徵。在 2010 年代,在其富有魅力的領導人伊藤穰一的指導下蓬勃發展,直到 2019 年,由於有爭議的財務關係,他突然辭職。
早期慈善方法(2015-2017)
-
到 2010 年代中期,科技行業的退出已經產生了足夠的個人財富,導致一些投資者開始嘗試傳統的慈善方式。
-
2015 年,Y Combinator 宣布成立一個非營利研究機構 YC Research,最初由其總裁 Sam Altman 個人捐贈 1000 萬美元資助。雖然沒有直接涉及科學(他們的首批研究項目集中在普遍基本收入、城市和人機交互上),但 YC Research 可以被理解為文化態度變化的風向標。正如 Sam Altman 在他的公告帖中解釋的那樣,有時「初創公司並不適合某些類型的創新」,這在當時是一種全新的觀點:
我們在 YC 的使命是盡可能地促進創新。這主要意味着為初創公司提供資金。但對於某些類型的創新來說,初創公司並不理想——例如,需要很長時間周期的工作,尋求回答非常開放性的問題,或開發不應由任何一家公司擁有的技術。
然而,他強調 YC Research 仍然旨在以不同於典型研究機構的方式做事(重點是我的):
我們認為研究機構可以比現在更好……研究人員的報酬和權力不會由發表大量低影響力論文或在眾多會議上發言來驅動——整個系統似乎已經崩壞。相反,我們將專註於產出的質量。
同年,馬克·扎克伯格和普里西拉·陳宣布,他們將捐出 99% 的 Facebook 股份用於慈善事業,這些事業由陳 - 扎克伯格倡議組織管理。與 Y Combinator 類似,陳和扎克伯格選擇以稍微不同的方式行事,將 CZI 結構設置為有限責任公司,而不是 501c3 非營利組織(像大多數慈善基金會那樣),他們認為這將給予他們「更有效地執行使命的靈活性」。
CZI 的首筆投資是一項 30 億美元的承諾,旨在「在我們的有生之年治癒、預防和管理所有人類疾病」,計劃在十年內分配完畢。其中 6 億美元被指定用於創建 Biohub,這是一個位於舊金山加州大學(UCSF)的研究中心,與斯坦福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合作建立。
在他們的聯合聲明中,扎克伯格解釋說,生命科學進展緩慢與當前科學資金和組織方式有關(重點是我的):
構建工具需要新的科學資助和組織方式……我們當前的資助環境並不真正激勵太多的工具開發……解決大問題需要將科學家和工程師聚集在一起以新的方式工作:共享數據,協調和合作。
次年,即 2016 年,肖恩·帕克創立了帕克癌症免疫治療研究所。帕克的聲明再次呼應了對科學研究方式的類似擔憂(重點是我的):
癌症問題不僅僅是資源的問題,而是我們如何分配這些資源的問題……這個系統在某種程度上是有問題的……負責資助大多數科學研究的機構通常不鼓勵科學家追求他們最大膽的想法,所以我們得不到雄心勃勃的科學。
與 2010 年代上半期相比,這一時期出現了對基礎研究資助的新興興趣,並且人們開始默認認識到初創公司無法完全實現目標——儘管捐助者強調創新研究文化本身的重要性,更加註重以科技為導向的產出、協作和工具開發。
大約同時期推出的其他一些反映這些趨勢的項目包括:
-
開放慈善:一個研究和資助機構,更廣泛地專註於改善慈善事業,但其最初的重點領域包括資助生物研究。開放慈善於 2017 年成為一個獨立組織,但它源於 Good Ventures(達斯汀·莫斯科維茨和卡里·圖納)與 Givewell 在之前幾年的合作。
-
OpenAI:一個非營利組織,最初被描述為「非營利研究公司」,於 2015 年由埃隆·馬斯克、薩姆·奧特曼等人以 10 億美元的承諾啟動。(OpenAI 後來轉變為營利性結構。)雖然不專註於科學,OpenAI 成為近年來科技領域最大的研究項目之一。他們的初始公告強調了開放出版、開放專利和合作的重要性。
在這個時期,儘管聲稱有興趣改善研究人員之間的合作,但似乎缺少了一件事——捐助者之間的協調。相反,人們感覺每項努力都以捐助者自身為中心,而不是共同通過多種方法解決一個明確定義的問題。
這並非是一種批評,而是為了突出早期主要捐贈者仍在學習如何通過非創業方式戰略性地解決科學問題,以及如何在傳統期望之外定義他們的慈善工作這一非常困難的挑戰——相比於今天的群體而言。
領域建設與新機構(2018-2021)
近年來,資助者和創始人之間的協調變得更加緊密,這有助於催生一系列新的科學計劃。
2017 年一篇 NBER 工作論文《創意是否越來越難以發現?》提出「研究努力正在大幅增加,而研究生產力卻在急劇下降」,引發了關於科學創新的 renewed 討論。2018 年,Patrick Collison 和 Michael Nielsen 在《大西洋月刊》上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其中包含的原創研究提出了類似的論點:儘管「科學家數量、科研經費和發表的科學論文數量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但我們的科學理解是否獲得了相應的增長?」
次年,Patrick Collison 和 Tyler Cowen 在《大西洋月刊》上發表了一篇相關文章《我們需要一門新的進步科學》,提出「世界將受益於一項有組織的努力來理解」如何實現進步,包括識別人才、激勵創新和合作的益處。
儘管他們的評論文章更廣泛地關注進步,但科學是一個突出的例子。Collison 和 Cowen 表示,「雖然科學產生了我們大部分的繁榮,但科學家和研究人員自身並沒有充分關注科學應該如何組織,」以及「對科學如何實踐和資助的批評性評估供應不足,這可能是出於不足為奇的原因。」
《大西洋月刊》的評論文章(加上大量後續努力)促成了「進步研究」社群的形成和發展,為那些對科學進步等議題感興趣的人提供了一個急需的思想家園和社區。
雖然當今的科學從業者並未正式隸屬於進步研究(大多數人可能會說他們不屬於這一領域),而且進步研究關注的問題遠不止科學,但我的感覺是,這樣一個社群的形成是有幫助的:
-
作為志同道合者的協調點,吸引更多人才進入該領域,並
-
使從業者的工作合法化。
2021 年,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參加了一個面對面的「科技瓶頸研討會」,其前提是瓶頸「存在於整個科學技術領域,解決這些瓶頸可能為整個領域帶來巨大進步」。與會者包括創始人和投資者,其中許多人已經在從事與科學相關的項目,包括 Fast Grants、Convergent Research 和 Rejuvenome。
研討會受到參与者的好評。它幫助更多人相互認識和了解,加強了對這個領域的共同方法和興趣,甚至激發了新的合作。
以下是近年來啟動的一些科學計劃。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共同的問題空間內實驗的多樣性,以及資助者和創始人之間加強的協調(注意各項計劃之間的重疊程度)。與 2010 年代更加單一、封閉的方法相比,這些都是一個健康、蓬勃發展的領域的跡象。

這些倡議大多集中在生命科學領域。我詢問了幾個人,他們認為為什麼會是這種情況。一些想法包括:
-
個人關係和興趣:一些資助者和創始人與生命科學領域有着預先存在的聯繫或背景。
-
講故事和公共敘事:生命科學意味着解決諸如治癒疾病、延長壽命、生育醫學和遺傳學等問題。與存在風險或太空探索相比,追求這類工作的益處更容易被公眾理解,尤其是在全球大流行之後。
如前所述,這個群體的特點是採用多樣化的方法:營利性和非營利性追求的混合,以及資助和運營組織的結合。我們還可以注意到在系統變革層面(組織 vs 個人)、研究類型(基礎 vs 應用)和項目時間跨度(短期 vs 長期)方面的多樣化方法。

為什麼今天有這麼多新倡議?
雖然長期以來一直有一群熱衷於科學的從業者,但只有最近的資金湧入才使得將這些長期存在的想法付諸實踐成為可能。(例如,Adam Marblestone 和 Sam Rodriques 在成功獲得資金之前已經思考聚焦研究組織多年。)
一些資助者傾向於淡化他們作為「資金提供者」的角色,但我認為強調良好資助實踐的重要性是很重要的。具體來說,我要強調的是,當今科技領域的科學資助者並非「向問題砸錢」,而是採取了戰略性的、但又經典的慈善方式來建立一個新的領域。兩項特別有用的主要努力為這一領域奠定了基礎:
-
更好的協調:資助方之間加強協調和共同出資,這有助於他們相互學習並做出更大的投入,同時也讓從業者在追求長期工作時感到安心;
-
領域建設:表明這些是有趣且值得研究的問題,吸引他人進入該領域並使從業者的工作合法化。
是什麼導致了對資助科學的興趣重新燃起?可能有幾個因素,其中一些是外部條件,另一些是有意識努力的結果:
全球新冠疫情
通過迫使人們應對龐大、不可改變的系統,疫情幫助我們意識到世界比之前看起來更加可塑。人們對官僚主義感到沮喪,無法擺脫這種官僚主義,並意識到他們可以立即採取行動——而不是在遙遠的未來——來改善現狀。
快速資助計劃是為了直接應對新冠疫情而啟動的,其成功似乎影響了 Arc 研究所的願景。長壽動力資助計劃也受到了快速資助模式的啟發,但關注的主題不同。
Arcadia Science 的創始人直接指出,新冠疫情「在我們通常的圈子之外,激發了對科學進步的緊迫感、協作精神和熱情。由此產生的疫苗研發展示了科學和科學家之間的合作能有多麼強大。」
我交談過的一個人認為,由於新冠疫情導致人們地理上分散到其他地方,這可能也產生了打破硅谷群體思維的效果,使人們接觸到新的思維方式,並使他們更容易接受非創業公司的方法。
成功的領域建設和參与者之間更好的協調
發表評論文章、舉辦研討會以及形成進步研究社區,使志同道合的人更容易找到彼此並進行協調。正如 Luke Muehlhauser 在他的 Open Phil 早期領域增長報告中指出的那樣,雖然這些方法可能看起來「顯而易見」,但它們也「經常有效」。
在我的交談中,長期從業者評論說,幾十年來人們一直對這個問題領域感興趣,但只是在最近幾年,他們才驚訝地發現(引用)「像我們這樣的人比我想象的要多。」
即使是多年來相互了解併合作的從業者之間,領域建設也產生了使他們的工作比以前更有地位的效果——更像是創業公司創始人——這將繼續吸引其他人進入這個領域。
在我們的對話中,有幾個人評論了這種效果。一個人說,這類項目(即開始一個雄心勃勃的非創業項目)直到最近還被認為是「無法獲得資金的」,因為現在有幾個人「讓它變得很酷」。另一個人覺得,雖然科技行業的普通人可能還不理解他們在做什麼,但他們感覺自己的工作不再被視為「低地位」。
加密貨幣財富繁榮
2017 年和 2021 年是加密貨幣財富創造的兩個主要轉折點。我們開始看到第一次繁榮的下游效應,並可能在未來幾年看到第二次繁榮的效應。
加密貨幣對科學資助領域產生了直接和間接的影響。首先,從實際角度來看,它創造了一批新的潛在資助者。當今活躍在科學領域的加密貨幣資助者主要是 2017 年第一次加密貨幣繁榮的受益者 - 就像馬克·扎克伯格、達斯汀·莫斯科維茨和肖恩·帕克是 Facebook 2012 年首次公開募股的受益者,並在幾年後成為活躍的慈善資助者。
其次,加密財富成為「傳統科技」在文化建設方面承擔更大風險的推動力。雖然很難證明這是真的,但我們可以將其視為奧弗頓窗口的轉移,即一個持有比中位數更極端觀點的群體的出現,可以使之前看似激進的立場變得合理可行。就科技而言,加密貨幣行業非諷刺地想要從頭重建社會的事實,使得比如說創立一個新的 501c3 研究機構看起來不那麼奇怪。
還有幾個宏觀條件可能促使科技界對資助新科學項目的興趣發生轉變:使資本變得廉價的牛市;普通民眾對傳統機構日益增長的幻滅感;2010 年代後期產生新財富的一波流動性事件;以及從 2010 年代中期開始科技與主流文化關係的根本性轉變。這些話題超出了我想在這裏討論的範圍,但值得注意,它們是其他促成因素。
衡量成功
最後,我想了解當今群體中的參与者如何看待衡量影響力。十年後,我們將如何知道這些努力是否成功?
幾乎每個我交談過的人都提到了某種版本的「1000 億美元問題」(這個術語歸功於 David Lang),指的是相比聯邦研發資金而言,私人資本相對較小,在美國每年達到 1000 多億美元。根據我們所能推測的,最新一波倡議總計代表了數十億美元的規模。雖然數額可觀,但與政府能做的相比只是一小部分。
由於這些相對的財務限制,我交談過的參与者反而在思考如何通過展示可能性來激發聯邦資金(特別是生命科學領域的國立衛生研究院資金)的改進,而不是試圖在資金上進行一對一的競爭。這種方法與慈善資本在公民社會中的角色更為一致,其目標不是與政府競爭或取代政府,而是通過不影響公共稅收的私人實驗來播種新想法。例如,美國的公共圖書館、公立學校和大學都是由早期的慈善工作塑造的。
選擇創辦公司而非非營利組織的從業者同樣受到延長資本壽命的願望驅使。如果一家公司成功了,它可以激發其他科技公司的創立,因為有大量的創業資金可用。相比之下,成功的非營利組織往往不會激發更多非營利組織的創立(即使它們會影響彼此的做法和興趣),因為慈善資本有限,這造成了一個更具競爭性的零和局面。
以下是我在交談中聽到的一些近期和長期目標,以及如何衡量這些目標的建議。

尾聲:DeSci 和新的加密原語
這個故事還有一個章節,我把它放在了單獨的「尾聲」部分,因為它既是新的,又與上述方法明顯不同,但也作為我們迄今為止所涵蓋的一切的重要對比。
如果我們放眼全局,考慮科學如何獲得資金和支持,我們可以採取多種方法。公共物品並非僅由政府資助;它們也可以受到市場(即創辦公司)和慈善資本的影響。到目前為止我們所看到的例子,無論看起來多麼新穎或不同,都屬於這些現有類別之一。
還有另一種更激進的方法,我將其(勉強地)稱為加密原生方法。這種方法的支持者認為,上述努力雖然是积極的發展,但最終複製了我們現有傳統系統的相同問題。他們會說,在不重寫其基本激勵機制的情況下創建新機構,從長遠來看無法解決任何問題:它只是重置了機構衰落的計時器。
即使在「傳統科技」群體中,對於「我們是在試圖創造新的公共機構,還是僅僅讓現有機構變得更好?」這個問題也存在廣泛的答案。一些倡議正在長期思考如何避免機構衰退,比如限制資金或組織規模。無論如何,我交談過的大多數人似乎都認同「1000 億美元問題」的方法:即高效地部署有限的資金,以在更大的聯邦層面產生影響。
相比之下,在加密原生方法中,支持者希望創造全新的公共產品資助方式。雖然他們與改善科學進步、吸引頂尖人才並將研究成果推向市場的長期願景相同,但他們的策略不同。他們的變革理論可能如下所示:
通過發明新的方式來獎勵科學家、改善合作、評估和提高他們工作的質量,確保科學進步能夠蓬勃發展,使他們能夠充分追求自己的好奇心,併產生能夠應用於造福人類的研究成果。
在我的對話中,我聽到那些支持不同方法的人幾乎一字不差地說:「學術界、研究界和政府的現有系統旨在產生某一系列結果。除非我們發明新的遊戲規則,否則什麼都不會改變。」然而,在傳統科技領域,似乎新的遊戲規則正在創造新的機構(但基本的組織原則被認為是靜態的),而在加密貨幣領域,則是完全設計新的激勵系統(其中組織原則被認為是可塑的)。
在 2021 年由 Protocol Labs 主辦的關於資助公共產品的虛擬會議「Funding the Commons」上,創始人 Juan Benet 發表了一個關於「跨越創新鴻溝」的演講。他指出,在過去十年裡,創業生態系統通過將新技術產品化,在研發創新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果。從他的角度來看,Y Combinator 對研發創新的貢獻遠遠超過了 Alphabet 或 Ethereum。

但是,雖然基礎研究努力集中在解決上述「藍色三角形」區域的問題,但它們並未解決缺失的「黑色方塊」:將研究轉化為現實世界的創新。正如科技生態系統為初創公司創造了數十億美元的風險投資資金,加密生態系統也可以為公共產品的資金做同樣的事情。
對我來說,這觸及了科技原生和加密原生解決公共產品問題方法之間的核心區別。在最佳情況下,科技方法是通過初創公司產生財富,然後將其剩餘財富用於慈善目的(無論是通過營利性還是非營利性倡議)。另一方面,加密方法是為公共產品創建一個原生資金系統,使參与者可以通過公共產品的開發本身來產生財富。
Vitalik Buterin 在 Funding the Commons 上的演講也呼應了這些觀點。他解釋說,區塊鏈社區更多地建立在公共產品而非私人產品之上,如開源代碼、協議研究、文檔和社區建設。因此,他強調「公共產品資金需要長期且系統化」,這意味着資金需要「不僅來自個人,還要來自應用程序和 / 或協議」。新的加密原語可以幫助解決這些需求,比如 DAO 或代幣獎勵。
加密和傳統技術原生方法之間的一些區別:
-
對有限上行空間與無上限上行空間的信念。傳統科技領域的人認識到 1000 億美元問題的局限性,而加密貨幣則對可能性持更廣闊的看法。我採訪的一位人士認為,加密貨幣網絡在未來十年可能會與聯邦資金水平相媲美。一套新的加密原語還將使大幅增加科學家的財務獎勵成為可能。無論這是否可實現,我都覺得這種對無上限上行空間的信念令人鼓舞。
-
人才的集中化與去中心化。如前所述,傳統科技似乎將精力集中在幫助那些正在被衰敗的官僚體制慢慢摧毀的優秀科學家。另一方面,加密貨幣採取了更加分散的人才方法,吸引並協調更大的貢獻者網絡。(正如有人告訴我的:「科學進步是一個協調問題。」)加密貨幣的方法旨在為世界提供工具,讓任何人都能進行實驗(最終會篩選出最佳人才),而不是主動識別和招募最佳人才進入組織。我們可以將此視為人才方面的開源 vs 科斯方法,這也是加密貨幣和傳統科技在更廣泛層面上的主題差異。
雖然傳統科技和加密技術為解決科學問題提供了兩種不同的方法,但資助者之間仍然存在交叉活動。資助者並不是根據他們的工作地點而歸類,而是基於變革理論的差異。一些資助者,如 Vitalik,可以同時支持傳統科技和加密技術的努力,這可以稱為改善科學的「多元化投資組合」方法。
進一步聚焦加密貨幣領域,有一個新興運動正在將新的原語應用於科學,這在 Web3 領域有時被稱為 DeSci,即去中心化科學。雖然並非所有人都認同這個術語,但在本節中我將用它作為簡稱來指代以加密為中心的改進科學方法,因為,嗯,它更朗朗上口。
令人驚訝的是,許多 DeSci 從業者都有科學背景。這些人不僅僅是決定將自己的技能應用於新行業的加密貨幣傳道者:還有一些科學家正在離開學術界或工業界的職位,全身心投入 DeSci。
Jessica Sacher,一位從微生物學家轉型為 Phage Directory 聯合創始人的人士,形容自己之前過着強烈的「模擬生活」:
我來自分子微生物學實驗室的工作台,在那裡我把實驗方法和數據寫在紙質筆記本上(在好日子里;其餘時間我寫在紙巾和橡膠手套上)。在實驗台工作的 7 年裡,我幾乎連 Excel 都很少使用。
儘管如此,她被去中心化科學(DeSci)所吸引,因為它提供了一種她在學術界無法獲得的樂觀願景(重點是我的):
[隨]着我花更多時間與科技 / 創業領域的人交流,我越來越意識到科學的問題來自人為的激勵系統,而不是來自宇宙的基本真理……對於已經[在科技領域]的人來說,這可能是顯而易見的,但對我這個生物學家來說並不明顯。
Joseph Cook 是另一位 DeSci 支持者,他是丹麥奧胡斯大學的環境科學家,專註於計算領域。雖然他和其他科學家一樣認為「我們當前的[科學研究]基礎設施已不再適用」,但他相信「去中心化模式可以用來重寫專業科學的規則」。
有趣的是,許多 DeSci 參与者似乎也具有生命科學背景,或專註於生命科學計劃,就像他們的傳統科技同行一樣。
雖然去中心化科學領域仍在發展中,以下是過去一年裡啟動的幾個實驗示例:
VitaDAO
VitaDAO 是一個由 DAO 管理的社區基金,「以開放和民主的方式資助和推進長壽研究」。他們在 Discord 上擁有超過 4,500 名成員,資助規模在 25,000 至 500,000 美元之間的項目。截至 2022 年 1 月,他們已資助了兩個項目,研究資金總額達 150 萬美元。
VitaDAO 的收入模式與 Thiel 的 Breakout Labs 類似,但帶有加密貨幣的特色:VitaDAO 成員擁有他們資助項目的知識產權(儘管他們表示這是可協商的),這理論上會增加 $VITA 代幣的財務價值。VitaDAO 與 Molecule 合作,後者自稱是「生物科技知識產權的 OpenSea」,開發了一個 IP-NFT 框架來管理其知識產權。(Molecule 正在為精神藥物研究啟動一個類似的項目,名為 PsyDAO。)
CryoDAO
CryoDAO 是一個由 DAO 管理的社區基金,致力於推進低溫保存研究例如開發新的低溫保護劑以降低毒性,或根據缺血情況制定不同的低溫保護方案。
CryoDAO 的目標是支持那些具有高潛力提升冷凍保存質量和能力的冷凍保存研究項目,低溫保存技術在可用性器官甚至人體保存領域有許多當前和潛在的應用。
OpScientia
OpScientia 是一個正在開發一套基於開放性、可訪問性和去中心化原則的新研究工作流程的平台。一些例子包括:研究數據的去中心化文件存儲、可驗證的聲譽系統和「博弈論同行評審」。
將 OpScientia 的語言與傳統科技在人才方面的變革理論進行比較再次很有用;OpScientia 將自己描述為「一個由開放科學活動家、研究人員、組織者和愛好者組成的社區」,正在「構建一個科學生態系統,解鎖數據孤島,協調合作並使資金民主化」。
LabDAO
LabDAO 旨在創建一個由社區運營的濕實驗室和干實驗室服務網絡,成員可以在其中進行實驗、交換試劑和共享數據。其創始人 Niklas Rindtorff 是德國海德堡德國癌症研究中心的醫生科學家。LabDAO 尚未正式啟動,但正在积極開發中,其 Discord 社區已有近 700 名成員。
Planck
Planck 希望通過將数字手稿放在區塊鏈上來改善科學知識的創造和獎勵方式,他們稱之為「alt-IP」。其創始人 Matt Stephenson 是一位行為經濟學家,他曾以 24,000 美元的價格出售了一個包含獨立數據分析的 NFT。
摘要
與往年相比,現在有了更多改善科學研究方法的途徑,這要歸功於:
-
宏觀條件的變化,如新冠疫情、科技領域的一系列流動性事件,以及加密貨幣的繁榮提高了可能性的標準;
-
有意識的領域建設努力(寫作、社區建設和會議)以使科學工作合法化並吸引人才進入該領域;
-
資助者(包括共同資助機會)和從業者之間更好的協調
如今仍有新的科學創業公司在建立,如 New Limit、Arcadia Science 和 Altos Labs。但現在也有研究機構的例子,如 Arc Institute 和 New Science,甚至還有加密原生實驗的新興例子,如 VitaDAO 和 LabDAO。並非一種方法取代了另一種,而是現在有更多的人嘗試不同的事物,這是一個不斷增長、蓬勃發展的領域的標誌。
科技行業仍然主要由初創公司主導,而且很可能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繼續如此。但隨着科技作為一個行業日趨成熟,以及出現更多極端財富結果,現在(正如人們所預期的)出現了越來越多利用慈善資本解決雄心勃勃問題的興趣。
加密貨幣通過開發公共產品的新原語將這一步推進得更遠。他們擔心傳統的慈善策略會重複傳統機構的錯誤,因此尋求開發新的方式來獎勵科學家並幫助他們分享無上限的收益,如果成功,這可能會為科學(和其他公共產品)帶來像創業公司為風險投資所做的那樣的影響。
加密和科技原生的變革理論存在根本差異。科技注重招募頂尖人才,但借鑒了當今科學和初創企業的類似獎勵結構。加密採取更分散、網絡化的方式吸引人才,並更願意重新構想專利、知識產權甚至研究實驗室本身等基本結構。這兩類從業者都相信通過外部工作來改善傳統機構。
在傳統技術方面,值得關注的是第一批「錨定」資助者是否能夠吸引更多資助者進入這個領域。如果他們的努力成功,我們應該會看到:
-
科學家發表高質量的工作,得到更廣泛科學界的認可;
-
新舉措持續吸引頂尖人才,被視為建立科學事業的理想場所;
-
由於展示可能性的新舉措,國立衛生研究院和聯邦部門其他地方發生了變化
在加密貨幣方面,我們應該關注新舉措是否:
-
能夠為科學工作生成和分配資金;
-
產生被更廣泛科學界認可的研究;
-
為參与的科學家產生無上限的獎勵(無論是財務上還是其他方面)
我特別感興趣的是觀察科技原生和加密原生方法之間的緊張關係如何展開。雖然它們處於不同的成熟階段,但從宏觀層面來看,這是兩個同時進行的重大實驗。
這個技術故事與過去幾十年的慈善努力相當吻合,這意味着它有更高的成功可能性:這是人們更容易理解的模式。加密貨幣的故事則截然不同,要求我們從一套全新的假設出發,重新想象資助和開發公共產品的含義。它更有可能失敗,或者只在有限的情況下成功。但如果它確實成功了,其潛在收益將大得難以想象。